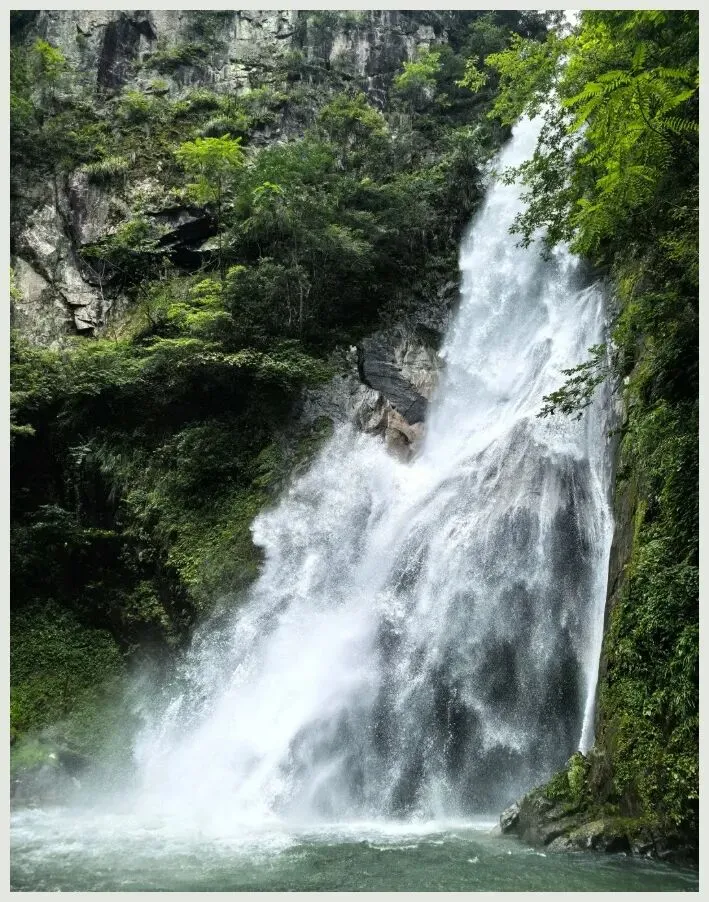株洲的风,总带着点旧铁皮的温度
走到博物馆铁门前,脚步忽然慢了
本来是跟着导航随便晃的,没打算停留太久。但看见那扇生了锈的铁门,门后停着的绿皮火车头露出半个身子时,脚步忽然就顿住了。不是刻意的,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拉住了似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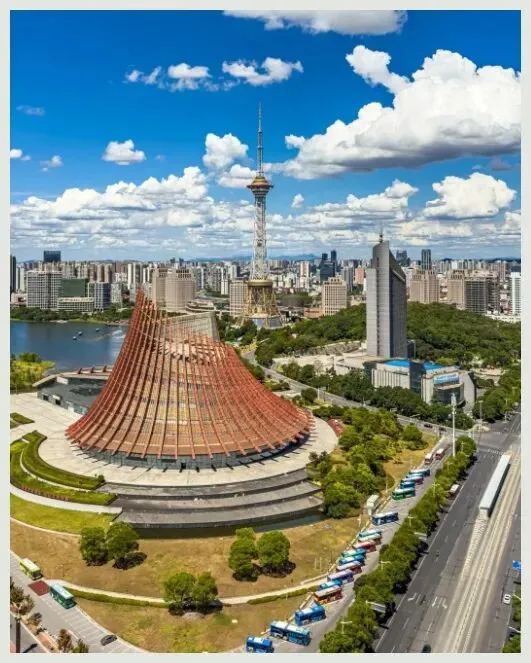
伸手碰了碰火车头的铁皮,凉的,指尖却好像沾到了一点机油的余味。旁边扎羊角辫的小孩仰着头问爸爸:“这是什么呀?”爸爸蹲下来,声音放得很轻:“这是以前拉货的火车,爷爷年轻的时候,就在这里上班呢。”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,落在铁皮上,斑斑驳驳的,像老照片里的光斑。我站了一会儿,没再往前走,只是看着那火车头,觉得它像个沉默的老人,守着这里的时光。
咸豆腐脑的热气里,早市醒了
早上七点多,肚子饿醒了,穿好衣服出门找吃的。拐过两个巷口,闻到一股浓得化不开的豆香,顺着味道走过去,就到了建宁路口的豆腐店。塑料棚子搭着,里面摆了几张矮桌和塑料凳,坐满了人。

要了一碗咸豆腐脑——本来以为会是甜的,结果老板撒上香葱,淋了一勺酱油。热气扑到脸上,我赶紧吸了一口,豆香混着酱油的咸,滑进喉咙里,暖得胃都舒展开了。旁边的阿姨边吃边跟老板聊天:“今天的豆腐脑还是这么嫩。”老板笑着说:“二十年了,都是这个做法。”吃完起身,早市已经热闹起来,卖菜的吆喝声、自行车的铃铛声、小孩的笑声,混在一起,像一首没谱的歌,却格外好听。
夜宿老楼,听见火车在远处呼吸
选民宿的时候,特意挑了靠近株洲站的老楼。房间不大,但很干净,窗户对着铁轨的方向。晚上躺在床上,翻了几页书,忽然听见“轰隆轰隆”的声音——火车来了。一开始觉得有点吵,翻了个身,却慢慢安静下来。

起身走到窗边,拉开窗帘,远处的火车灯亮着,像两颗移动的星星,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楼下的夜宵摊还没散,飘来剁椒蒸腊肉的香味,有人在小声聊天,偶尔传来碰杯的声音。我靠在窗边,听着火车的声音,居然觉得很踏实,像回到了小时候,外婆家旁边的铁轨,晚上总能听见火车过,那声音是安心的。
风把头发吹乱的时候,我不想走了
离开株洲的前一天下午,我走到了湘江边。风很大,吹得江面上泛起层层波浪,也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我找了个石凳坐下来,看着江水慢慢流,远处的桥上车来车往,却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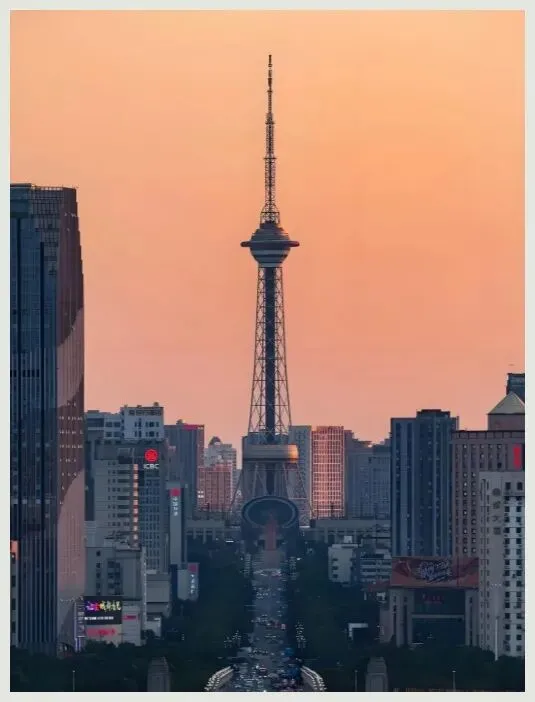
旁边有个老大爷在钓鱼,鱼竿架在那里,他却闭着眼睛晒太阳。我问他:“这里的风总是这么大吗?”他睁开眼,笑了笑:“是啊,株洲的风,带着点湘江的湿气,还有老厂房的味道。”坐了大概一个小时,太阳慢慢沉下去,把江水染成了金色。我起身准备走,却有点舍不得——舍不得这里的风,舍不得咸豆腐脑的热气,舍不得火车的轰隆声,舍不得那些坐在塑料凳上聊天的人。
最后离开的时候,我没买什么纪念品。只是把株洲的风,藏在了头发里;把咸豆腐脑的味道,记在了胃里;把火车的声音,留在了耳朵里。这城不热闹,也不张扬,却像一杯温茶,喝下去,暖到心里。下次再来,我想慢慢走,不用赶时间,就像这里的人一样,稳着走,挺好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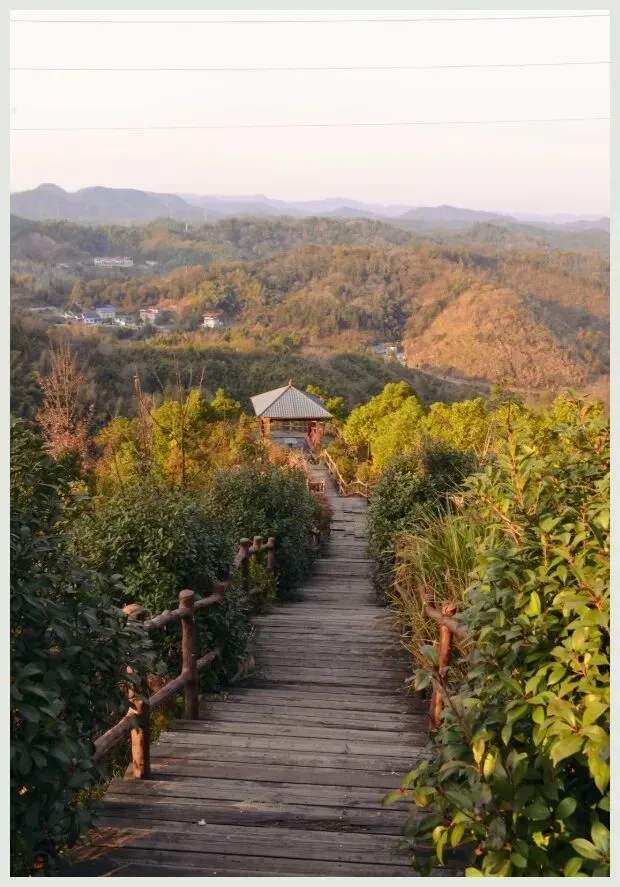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